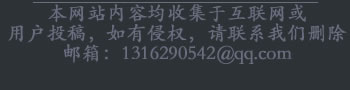画报作为新闻媒介的一种,在中国勃兴于晚清时期。现在已知的晚清画报有120种左右,其中当年有过重要地位、现在存世量也较多的画报,约有30种。这些画报中有着大量关于晚清的影像资料,为我们直接观看晚清提供了可能。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过去的20余年间,对晚清画报有着持续的关注和研究。最近,他将相关研究结集成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》一书,由三联书店出版。12月9日,在国家图书馆学津堂举行的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》新书发布会上,陈平原和现场读者分享了他晚清画报研究中的一些成果和心得。
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——晚清画报研究》,作者:陈平原,出版社:三联书店,2018年10月
画报是以“画”为主体的新闻媒体
中国历来有“左图右史”之说,实际上“图书”一词本身就表明,有图的书不可谓新事物。画报之为画报,陈平原说,不在于其中有“画”,而在于它是以“画”为主要叙事媒介的“报”。“报”意味着画报需要有新闻性,而“画”区别于报纸的插图,往往是画报的主体而非单单用以图解文字。
画报以“画”为主体,也就意味着读者不需要有太高的识文断字水平。“不特士夫宜阅,商贾亦何不可阅?不特乡愚宜阅,妇女亦何不可阅?”将商人、妇女、乡下人统统视为自己的潜在读者的画报,迎合的是国内市场,反映了大众趣味。“天下容有不能读日报之人,天下无有不喜阅画报之人”,《点石斋画报》曾有这样的评说。因此,透过画报,我们可以更切近地了解晚清时期的大众心理,知晓什么是他们关心的和感兴趣的,什么是他们认为新奇的和可资谈论的。
《点石斋画报》上的《赛马志盛》。创办于上海的《点石斋画报》内容多有描绘西方现代事物者,如此处的跑马即是。
不难想到,以“画”为主体的画报,对于画师的依赖程度,远大于对文人的依赖。毕竟,通文字者多,能作画者少。关于画师地位更高这一点,甚至可以从署名中略见一斑。上海《点石斋画报》4666幅图画中,画师可考的有4609幅,超过98%,而文字作者则几乎全不可考。
《点石斋画报》上的《操演水龙》。水龙即消防队救火用的水喉。消防队及其相关设备都是现代西方新事物的代表,画报开篇即言“西人善用火而亦善防火”。
有点特殊的是北京的画报,根据刊头或正文,我们能判断《星期画报》乃“杨采三演说”,《益森画报》是“学退山民编撰”,《正俗画报》的发行兼编辑雷震远、《醒世画报》的编辑则是张凤纲。可即便这些署名的文字作者,比起同一画报的画师如顾月洲、刘炳堂、李菊侪、胡竹溪等来,也都不太重要。
北京的《醒世画报》写明编辑者(图片上方正中位置),画师名字则在左下有记录。
而广州最重要的画报《时事画报》,其创办人则干脆为26位专业画师。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画作的看重,甚至有图文全不相关的情况。陈平原说他一开始曾费心考虑过,为何某文要配某图,后来明白了,《时事画报》中有时图文是无关的;之所以要将某幅画作放入,全因兼任编者的画师认为自己的那幅作品好。
广州《时事画报》列有“本报美术同人表”,写着各画师及其专长。比如林璞初工人物,而李鳌擅山水。
以新闻性作为画报第一要义,来考量晚清的出版物,则1884年5月8日在上海创刊的《点石斋画报》可谓画报鼻祖。而整个晚清时期,上海、北京和广州是画报最为兴盛的三座城市,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,其画报也值得留意;而其他城市虽也偶有刊行画报的,如成都的《通俗画报》、杭州的《新闻画报》以及汕头的《双日画报》、《图画新报》等,但大都发行时间短,影响也不大。而作为晚清画报研究的终止点,陈平原选在1913年而非清帝逊位的1911年,理由是晚清很有影响的石印画报《醒华画报》、《浅说画报》和广州《时事画报》均发行至1913年,而摄影的日渐普及,取代了画家之笔,画报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围观女学生放学,曾是晚清男人的消遣
《点石斋画报》1884年5月8日在上海创刊,经正女塾1898年5月31日在上海正式开学,无论是办画报,还是开设女子学堂,北京都落在上海的后面。但庚子事变是一个转机。“庚子事变的时候,皇帝都跑了,两年后才回来。回来的时候必须改革。”陈平原说,北京的改革是被打出来的改革。1902年后的北京生机勃勃,办学堂、办杂志都被允许了,可以做各种在上海已经有的一系列的改革。
陈平原以18种在北京出版的画报,按照创刊时间排列,看他们怎么介绍北京的女子学堂的兴起,以及女子学堂如何受制于当初大的政治环境,尤其是朝廷的影响。
晚清兴办女学堂,最缺的是合格的教师、教材和教室,以及充满求知欲的女学生。这些朝廷都关心,但对于女学生的着装,朝廷尤为在意。因为过去女子养在深闺中,如何着装是私事,现在去上学,就意味着要抛头露面,女学生如何着装关系到对社会风气的影响。为此,朝廷曾有非常详细的规定:女学堂的制服必须用长衫,长度则要过膝,四周均不开衩;服装的颜色,冬春两季用蓝色,夏秋两季用浅蓝色;材质以本国土产的棉布和夏布为宜;另外不得涂脂抹粉,不得簪花,不得穿洋服。
男人不得随意出入女学堂;教师的选用上,也严加防范,规定授课的男性,需为50岁以上。“假定是50岁以后的男人不会有邪心,这样的话,教学比较放心。”陈平原说。但是一方面不让男人进女学堂,一方面又要向男人募捐学堂经费,于是每年选定时日作为开放日,请人来学堂参观教学成果——女学生并不在场,只将课业放在桌上,供人览阅。
但若是想看女学生,并不非要进到学堂内,可以在学堂外等女学生放学。这样的民众相当多,以至于朝廷曾考虑将女学堂与热闹的街市相隔绝,并规定女学生要有家人或者仆人来接。1907年《日新画报》上的一幅《不开通》,讲的就是围观女学生放学:“甘石桥第一女学蒙养院,每日下学时候,街上人挤了个满儿,简直的过不去人。看学生虽是好事,可也别妨碍交通呵。可是该处守望的,也该竭力的劝劝才好。”
《不开通》展示的围观女学生的男人
陈平原另外举了北京的《开通画报》第8期上的《花界热心》,来展示男性对女性的观看:
《花界热心》
画报配文说:“自从江北遭此惨状,北京各色人等,都发了善念。惟妓女向例热心,因江北饥民大家商议大开演说会,上捐的人颇踊跃。”陈平原评论道:“很可惜,如此激动人心的场景,被画面右上角那手持望远镜的男子给破坏殆尽。人家在募捐,他在看什么?不外是尽情欣赏那‘盛装表演’的妓女。”
这里陈平原似有误读。所谓“如此激动人心的场景”指的难道不正该是“‘盛装表演’的妓女”吗?何以拿望远镜窥看的男子对于这激动人心的场景是一种破坏呢?他不正构成这一场景的一部分吗?画面右侧台子上的“演说会”三个大字,表明那里也是在募捐,然而捐者寥寥;而左侧因为是“花界演说募”,捐者众多。都是一样的募捐,左侧捐款者多而右侧寥寥无几,可见“激动人心”的不是大家对于灾民的热心,而是正在募捐的花界美女。
这些男子在街头看女学生和募捐的妓女,因为这是不多的观看漂亮女性的机会,而画报画出他们的观看,以便画报的观者可以看到他们所看的——女学生和妓女。这些画报,作为媒介,正在记录一个不透过媒介而直接观看的时代,这一没有媒介、必须亲身观看的时代将在画报、照片和流动影像等媒介兴起后,渐渐远去。
但不管怎样,京城花界在着装一事上似终究不敌女学生的魅力大。陈平原展示了北京《醒世画报》上的一幅《鱼目混珠》:
《鱼目混珠》
画面上的文字告诉我们,两个妓女的衣着打扮像女学生,以至有“鱼目混珠”之虞。这与上海的情况很不一样,陈平原说,上海引领服饰风潮的是妓女,上海的女学生穿得像妓女,而北京的妓女穿得像女学生。
郭沫若就曾讲起自己小时候最爱跑到学校里看女学生操练,陈平原说,晚清有两门课是新设的,一是唱歌,一是体操,而出操的时候穿的衣服,为了活动方便,一定是紧身的。女学生出操作为值得一看的对象,甚至被制成了年画:
《女学堂演对图》
“大家想象一下,印成年画,花花绿绿的,很好看。”陈平原说。他似乎是希望我们留意,在晚清,作为观看对象的女学生是怎样地被着力呈现的,即不仅要画下来,而且要上色——晚清画报都是黑白的,只有个别画报封面是彩色的,而女学生是够格被以彩色呈现,制成年画贴出来的。
陈平原说,这些戴着西洋帽、提着手杖、挎着枪和刀的女学生,她们在年画里固然是被观看的对象,然而她们毕竟已经进了学堂,读了书,操练了身体,她们将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扮演角色,发挥力量。
实际上,晚清画报上不仅有作为风景被观看的女学生,也有古代的女英雄,如花木兰、冼夫人和秦良玉,还刊登西洋的女英雄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。
《罗兰夫人》
秋瑾的慷慨就义,以及追慕秋瑾的姐妹们每年在西湖边给她进行的公祭,也都在晚清画报上刊登。
《秋瑾女士之历史》
受过教育的女学生,逐渐在社会政治运动中显示自己的力量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,上海医院医学堂的女学生和另外一些女学堂的毕业生,组成红十字会,到武昌前线帮助革命军:
《战时赤十字会起矣》
上海还有组成娘子军,准备参与到武昌起义里去的:
《上海娘子军》
下面这张画报表现的是天津的事。辛亥革命成功了,女子师范学堂的女生提灯上街庆祝中华民国成立:
《女子提灯会》
陈平原说,晚清时期,在尘土飞扬的北京大街上身着崭新校服的被围观的女学生,那时也正在逐渐走出深闺。十几年后,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,她们登上了文学、教育乃至政治的舞台,展现其身姿和力量,一举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。而这一女学生从被观看到显示其力量的历史,被画报完整地捕捉了下来,值得我们探究。
(延伸阅读:《这些19世纪的摄影,塑造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 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国内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有关中国的19世纪老照片,与面向国内读者的画报不同,19世纪的中国照片,多由外国人拍摄,面向海外市场,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照片中的晚清和画报中的晚清的不同,详情可参看本频道之前的报道。)
作者:新京报记者 寇淮禹
编辑:徐悦东 校对:翟永军